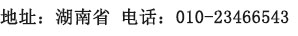肝气虚
柳暗花明又一村:
肝气虚病证的发现与治法方剂的创新
从事中医学习、研究与临床35年来,让我难以忘却的事情,往往是面对患者的病情,开具的处方没有效果,甚至是长时间没有效果,或病情反而加重了。无效医疗的问题,几乎每天困扰着我的临证实践。
尤其是面对大量慢性良性疾病患者,临床有多种不适症状,给患者带来几年或几十年痛苦,而不能发挥好中医优势取得好的效果时,让我不得不对其深刻思考。
30多年前,一位亲戚经常出现口苦发涩、烧心、胃胀等不适,共吃了10个月左右的中药,但一直没收到理想的效果。又过了2年,当年种的山楂大丰收,却没有销路,亲戚怕浪费,就天天煮着吃吃了一整个秋季和冬季,结果胃病好了,平时出现的口苦发涩、烧心、胃胀等症状也全部消失了,吃饭十分香甜。
通过这个案例,我悟出了两个道理:一是山楂是酸性食物,常吃山楂中和了胃里过多的碱性,故使平时的症状消失;二是许多过去没见过的新病、疑难杂症,与“吃”相关,由于时代、饮食习惯、生活方式的不同,会产生不同的“时代病”。由此,我总结和创新了治疗肝气虚病证的治法方剂。
1.酸味食物和中药的独特作用
酸、苦、甘、辛、咸五味人五脏,酸入肝,补肝是中医学的基本理论之一,它既是古代医家临床实践的总结,更是古代劳动人民饮食文化的积累与反映。
人类在进化过程中,对饮食的自然选择,有很多是酸味的食物(包括自然的和人工制作的):相对而言,很少选择碱性发涩的食物。若把传统的饮食观念与中医学酸入肝的理论相联系,与中医临床实践相联系,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和
深层次的理解。
回顾临床积累的消化不良、胃酸分泌减少缺乏性胃炎、胆汁反流(或糜烂)性胃炎、慢性萎缩性胃炎等,以胃酸分泌减少、消化能力下降、胃肠动力障碍为特点的胃病患者的治疗病案,其中酸味食物和酸味中药在治疗过程中显现出了独特的功效;而这方面起初的经验,多是来自患者自身的体验。
这类胃病的一些症状如纳呆、食少、胃腹胀闷或疼痛、呃逆、恶心、干呕、或呕吐黄水、烧心、口干、口苦,或呕吐苦水、口涩等,患者经过一些饮食结构的调整后,会有明显减轻或缓解。
例如,有的患者喜欢多吃醋,甚至喜欢喝点醋,胃会感到舒服,纳呆好转,饭量增加;有的患者喜欢喝酸奶或果汁果醋饮料,胃腹胀闷或疼痛会减轻;有的患者喜欢吃话梅、西红柿等,呃逆上气会缓解;有的患者喜欢吃山楂、酸菜、泡菜等发酵的酸味菜,烧心、口干、口苦、口涩或呕吐黄水等症状会好转。
当然也有一些患者,有因食某些食物而病情加重的情况,如吃香蕉、柿子后,口涩、胃腹胀闷或疼痛会反复;喝鲜奶、豆浆或吃油腻食物等,会出现恶心、干呕,甚至呕吐;食用含碱或苏打的稀饭、面食、饼千、点心或饮料后,烧心、口干、口苦症状会加重等。
通过总结这类胃病的治疗与患者的饮食体验,不难发现一个规律,即饮食偏酸性,能起到有效的治疗作用,偏碱性会加重病情,这与酸碱中和的朴素道理是一致的,因此用抑制胃酸分泌的药物,和碱性药物通治一切胃病显然是不正确的。
2.肝气虚病证的发现与治疗方剂,酸味补肝汤的创立
中医学中没有“碱”的概念,但有“涩”味的认识。实际上“涩”味与“碱”的性是相通的。如生活中柿子不熟时碱性较大,咬一口则满嘴发“涩”。要解这“涩”味,喝口淡醋漱口就能消除,这是因为酸味与涩味相反,酸味能解涩味,这与化学中酸中和碱的实质是一样的。
在临证过程中可发现,“口苦、口涩”等病症,按传统的中医学理论辨证分析,是无法对号入座的,故用原有的中医辨证理论治疗“口苦、口涩”等病症,用药后的效果不佳。反思之余,我逐渐形成了肝气虚的病证思路和观点。
通常饮食结构偏酸为主者,对胃病出现的“口苦、口涩”等病症具有明显的治疗与预防作用,因此,选择适当的酸味中药治疗此类胃病及“口苦、口涩”等病症,《中药学》载有约种药物,有26种具酸味,其中18种归肝经。
这26种酸味药中除去外用药和兼涩味的药,余下的白芍、木瓜、香橼、山楂、乌梅、川牛膝、赤小豆、五味子、山萸肉等这些酸味药物,治疗胃酸分泌缺乏减少,而有明显碱性液返流的胃病,症状如口涩、口苦或呕吐苦水、呕吐黄水、烧心等有明显效果。
续
(与吞酸、吐清水引起的烧心相反)等,有明显的效果;若再辅以辨证施膳、调整饮食结构(以“偏酸不吃咸”为原则),则疗效会进一步提高。
由此可推论:既然酸味药入肝、养肝、补肝,能治疗肝气虚,用于治疗口涩、口苦(或吐苦)、吐黄、(碱性)烧心等症状效果显著,那么口涩、口苦(或吐苦、吐黄、(碱性)烧心等就应当是肝气虚的病症,其发生机制如下。
口涩:表现为自觉口舌发涩,或舌体感觉板、厚,或有粗糙感,或伴辣感,常于晨起前后明显,情志不舒、饮食不节加重。其病机为肝气虚则疏泄功能下降,中焦气机不畅,引起脾主运化水湿功能异常,脾土侮肝木,郁久生热化火。
口苦、吐黄:表现为自觉口苦或口吐黄水明显,常于晨起前后、饭前明显,情志不舒、饮食不节加重。其病机为肝气虚则疏泄功能下降,胆汁排泄功能异常,导致胆汁不下而返至胃,使胃主通降功能失常,胃气上逆,胆汁随胃气上溢于口则口苦,甚则呕吐黄水。
烧心:表现为自觉胃热或烧灼感,甚则连及咽喉、口舌,常伴口涩、口苦、口干,多于饭后、饮食不节、情志不舒时加重,或半夜前后发作。注意本症与烧心伴吞酸、吐清水之症不同。其病机为肝气虚则疏泄功能下降,胆汁排泄功能异常,胃主通降功能失职,胆汁郁而化火则烧心;胃气上逆,则烧灼感连及咽喉、口舌。
肝气虚引发的以上病症的基本病理机制,皆为肝气虚弱,肝主疏泄功能下降,导致中焦气机枢纽运转失灵,升者不升,降者不降,通路不畅,引起脾主运化水湿、胆主排泄胆汁、胃主通降功能异常。
回顾文献,治疗肝虚、肝气虚的治疗大法和组方用药原则,早在《金匮要略》中已有明示:“夫肝之病,补用酸,助用焦苦,益用甘味之药调之。酸入肝,焦苦人心,甘入脾肝虚则用此法,实则不再用之。经曰:虚虚实实,补不足,损有余,是其意也。”这与临床实证分析的结果一脉相承。
由此,结合临床,我将治疗肝气虚的具体用方拟为酸味补肝汤。其药物组成为:
白芍15克、山楂12克、木瓜9克、香橼6克、乌梅6克、川牛膝6克、赤小豆6克、五味子3克、山萸肉3克、栀子3克、山药3克、甘草3克。
具补肝气、强疏泄之功效,主治肝气虚引起的口涩、口苦(或吐苦,吐黄、(碱性)烧心等病症。
方中白芍苦酸微寒,归肝脾经,为主药,其酸入肝能补肝气、强疏泄,恢复肝主疏泄的功能,保持中焦气机枢纽运转畅通,从而使脾能升、胃能降,胆汁下排而不上逆;其寒能制热,制胆汁之郁热。
山楂,酸甘微温,归脾、胃、肝经,其味酸入肝能补肝气、强疏泄,为消油腻积滞之要药;木瓜酸温,归肝、脾经,其味酸能入肝而补肝气、强疏泄,又能和胃化湿而治吐;
香橼辛微苦酸温,归肝、脾、肺经,其味酸入肝补肝气、强疏泄,又能疏肝理气和中,调畅中焦气机枢纽。此三味辅助主药,共为臣药。
川牛膝,苦酸平,归肝、肾经,其味酸入肝而补肝气、强疏泄,又功擅苦泄下降,能引血下行,以降上炎之火,灭胆汁淤积于胃所化之火;乌梅酸平,归肝、脾、肺、大肠经,其味酸入肝而补肝气、强疏泄,又能生津止渴;
赤小豆甘酸平,归心、小肠经,能利湿退黄;五味子酸温,归肺、肾、心经,可生津止渴,又能滋水涵木,还能敛金扶木、宁心安木;山萸肉酸微涩,归肝、肾经,其味酸入肝而补肝气、强疏泄,又能滋水涵木。
上五药助君臣之力,共为佐药。
上述九味药体现的是“夫肝之病,补用酸”的原则,“助用焦苦”则选栀子,其苦寒,归心、肺、胃、三焦经,既可清三焦之热与火,又能清利湿热、利胆退黄;
“益用甘味之药调之”选山药,其甘平,归脾、肺、肾经,可益气养阴;甘草甘平,归心、肺、脾、胃经,可调和诸药。以上诸药配伍,方证相合,药证对应,疗效显著。
酸味补肝汤的组方,一是基于中医学“酸入肝”的理论,二是基于张仲景治疗肝虚的组方原则;三是基于大量临床病例经验的总结;但本文论述的肝气虚的病症与酸味补肝汤,是中医理论中较特别的一组病症和方剂,没有可借鉴的经验和研究,仍需进一步在理论研究和临床应用中进行证实和深化。
在以上大量治疗胃病经验的基础上,我把中医学酸味入肝、补肝、养肝的理论与化学酸碱中和的理论相结合,推证出了肝气虚病证应有的临床表现,又在张仲景理论指导下,确立了治疗肝气虚的用方,酸味补肝汤,并通过临床应用及疗效进行了验证,以补中医学肝气虚病证理论之缺。
来源明中医之路第二辑
转自绞尽脑汁张庆军
苏轼一生的书法
本